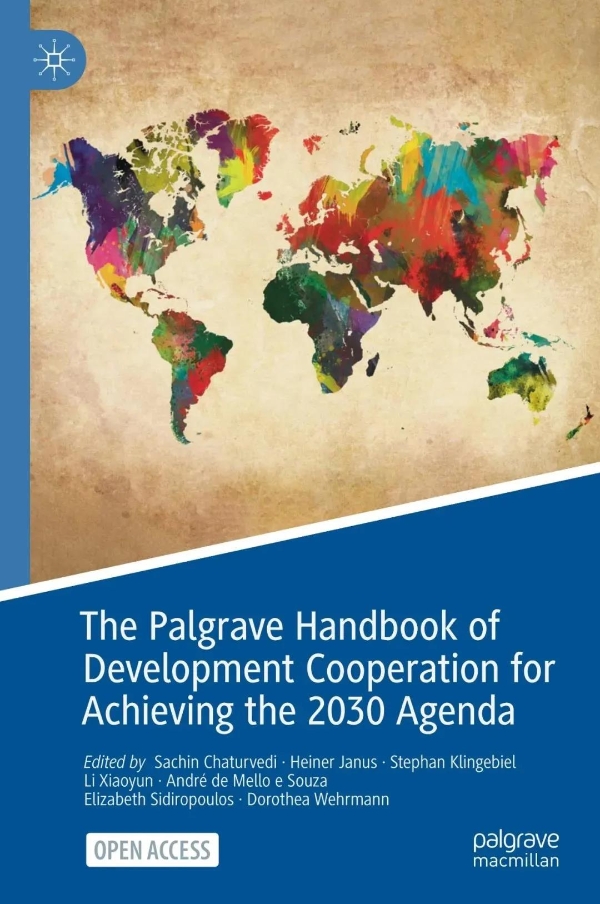【CIDGA】新书:富含争议的全球治理背景下的发展合作
引言
由我院名誉院长李小云参与主编、多位团队成员参与写作的《竞合:帕尔格雷夫发展合作手册》(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for Achieving the 2030 Agenda: Contested Collaboration)一书近期出版,该书旨在通过阐述各方学者就如何管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来推动发展合作领域从业者和研究人员之间的讨论交流,孕育新发展知识。我院教授参与编撰该书的四章,分别为第一章:富含争议的全球治理背景下的发展合作、第十章:中国与经合组织援助国发展合作的吸力石、第十八章:中国是否应该加入全球有效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第三十三章:推进2030年议程的发展合作经验。本公号陆续推出摘要以飨读者。
富含争议的全球治理背景下的发展合作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ontested Global Governance)
发展合作蓝皮书从可持续发展议程中诸多具体可测量的目标,及相应的指标融入手,探究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人们普遍认为,可持续发展议程是为了实现全球共同利益的国际合作。然而就目前而言,全球整体合作呈现碎片化的格局,发展合作领域尤其如此。在此情境下,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为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如何协调发展合作中的不同叙事与规范成为亟待探索的一大问题。
本书试图在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首先,近年来多边合作机制严重弱化,发展合作话语发生诸多变化,本书对发展合作政策领域中关于塑造多种合作方式的叙事和规范进行了详尽阐述。其次,叙事方式的不断变化加剧了不同发展合作规范间的竞争,本书详细讨论了新旧制度的竞争场域。最后,本书探讨了在国际治理结构中如何更好地参与竞争并推进合作。
具体而言,本书各章涉及以下方面:国际关系与(全球)集体行动中观念的兴起(规范的生成与传播)、(全球)解决方案的创新、全球公共物品和共有物品,以及全球治理背景下不断变化的发展合作环境。各章对发展合作持有不同的理解角度,使用全球治理研究的不同概念,展示竞争性政策领域的知识概况。因此,无论从广义或狭义上看,诸多发展合作方式展示了不同层级的权力转移和多元叙事。对这些竞争性合作场域的理解,将有助于更好地协调发展合作中的多元叙事和规范,从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本章节英文版下载链接(点击阅读原文下载):
https://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978-3-030-57938-8_1
【CIDGA】新书系列二:中国是否要加入全球有效发展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是否要加入全球有效发展合作伙伴关系(GPEDC)?中国和全球有效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前景展望
(Should China Join the GPEDC? Prospects for China and th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Effectiv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李小云 齐顾波
2011年,第四届援助有效性高级别论坛在韩国釜山举行,全球有效发展合作伙伴关系(GPEDC)第一届高级别会议也顺势启动,这一活动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转折点,实现了从援助有效性向发展有效性的转变。第二届高级别会议于2016年在内罗毕举行,总结回顾实施援助有效性议程和发展有效性议程十年来获得的经验教训。两届会议均吸引了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国际发展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多种类型发展主体的参与。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该合作伙伴关系仍然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对其存在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并拒绝参与其中。
本文重点分析了新兴国家对该伙伴关系持质疑态度的原因。其次,文章还深入探讨了GPEDC是否是全球发展的有益平台,以及多种利益主体是否可以在这一新框架下开展合作。最后,文章还进一步说明了如何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和环境下开展合作。文章发现,新兴国家普遍认为GPEDC是DAC进行扩张的另一种形式,更倾向于制定有利于OECD-DAC成员国的决定,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其援助原则和范式,以分担DAC数十年来积累的沉重负担,对GPEDC存在的合理性提出质疑。
事实上,GPEDC是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确立的全球平等伦理发展起来的机制,尽管有政治意图,由发达国家主导,且存在对其有效性的争论,但其重点关注全球发展,覆盖范围和领域广泛,在发展援助方面已积累丰富经验,在全球发展架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相比之下,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主要通过南南合作方式来影响全球发展议程,强调贸易和投资发展,不仅改变了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还重塑了全球发展治理架构。然而,由于其经济实力较弱,在知识生产、管理和人力资本等方面发展有限,对现有的发展合作架构仅能起补充作用。
在此背景下,本文建议中国等新兴国家应积极参与GPEDC,共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与此同时,为使新兴国家积极参与GPEDC,并使GPEDC更具包容性和更加有效,本文建议,首先,GPEDC应积极与新兴国家开展对话;其次,GPEDC应提出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新兴国家感兴趣的议题;建立工作组,与新兴国家开展对话;明确阐明GPEDC与UNDCF、G20发展工作组的联系等。
*本章节英文版下载链接(点击阅读原文下载):
https://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978-3-030-57938-8_18
【CIDGA】新书系列三:中国对外援助与西方国家对外援助是趋同还是分野?
中国和经合组织援助国的发展合作的基础:吸力石分析框架
(Conceptualising Ideational Convergence of China and OECD Donors: Coalition Magnets i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deational Convergence)
Heiner Janus 唐丽霞
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以及中国在国际事务参与度的不断提高,引发了学界关于中国作为新兴国家在参与全球发展合作事务中所扮演角色的激烈辩论。尽管中国和经合组织捐助国之间存在长久分歧,但近年来,中国和发展援助委员会捐助国在多个合作领域的援助活动中逐渐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重合。
本文主要围绕发展援助委员会捐助国和中国等非发展援助委员会捐助国在话语、动机、规范、条件约束、主题领域、制度结构和模式方面的趋同或分歧等展开探讨。本文将“吸力石”理念框架应用于互惠互利、发展成果和2030年议程这三个理念中,并分析政策发起者如何将理念与战略相匹配以促进融合和变革。此外,本文简要概述政策发起者在当今全球发展合作的大背景下如何联系国内和全球议程,从而以明智的方式促进融合。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对中国对外援助理念和制度进行背景介绍。其次,定义“吸力石”概念并梳理相关分析框架。随后,识别三大“吸力石”:互惠互利、发展成果与2030年议程,并探讨其在促进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和中国参与发展合作中的潜在效能。最后,基于当前发展语境,对本研究进行总结。
互惠互利理念在发展合作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锚定在南南合作和中国对外援助中。此理念蕴含多种含义,涵盖中国对外合作交流的多个方面,包括对外援助。并且中国、其他南南合作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捐助国对此存在不同理解。中国和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捐助国在不同的政策文件中将互惠互利理念合法化。发展成果理念要求从财务、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个方面不断衡量对外援助的绩效,具有被政策发起者用于促进融合的战略潜力。此理念是多义的,涵盖多个维度,各个利益相关者对其有不同的理解。无论在发展援助委员会捐助国还是在中国,发展成果理念在不同的政策文件中都具有很高的合法性。2030年议程是一个高度通用和多义的理念。它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普遍认可,并被赋予保护地球与促进人类发展的厚望。它也是多义的,因为没有任何国家被强制要求执行每一个目标,而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优先考虑并执行议程的某些部分。同样也允许不同的参与者用自己的理解去思考如何实现此议程。
虽然这些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和发展援助委员会在提供对外援助上有了更多可以合作和互动的基础,但是基于注重融合话语的协调和交流的需求,以及在国家层面政治与多边主义之间的分歧日益扩大的背景下,每个理念(互惠互利、发展成果和2030年议程)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互惠互利理念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经济利益的过分强调有可能出现因谋求私人利益而选择发展议程的局面;二是发展合作中的权力关系仍然主要偏向援助提供者,而受援者的代理和心声并未得到有效保护,难以实现真正的互惠互利。发展成果理念存在的主要挑战是: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捐助国和中国在援助有效性评估指标方面稍显落后。2030年议程现已存在广泛的融合空间,但政策决策者们面临以协调的方式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开展工作的挑战,需要根据这些背景并通过能使公众更广泛地参与和认识的方式不断重构2030年议程理念。
虽然这些理念还不能让中国和国际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在国际发展援助上完全达成共识,但是这些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了广泛的影响力和认可度。如果政策决策者能策略性地加以运用,就可以将国际规范与国内政治和社会变革进程相联系。“吸力石”理念是分析国际发展合作挑战的有用框架,且在经合组织捐助国与中国的立场不一致时尤为有用。基于对此理念的评估,文章总结了其对于促进不同政策偏好趋同的作用。首先,“吸力石”理念具有将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和中国围绕政策评估集聚在一起的潜力。第二,即使在民族主义倾向盛行的全球环境中,“吸力石”理念也可以成为实现政策变革的有效工具。对于政策发起者而言,关键是通过针对性的政策信息,将政策与沟通话语相结合。
此外,2030年议程作为一种新的可持续发展范式,已得到联合国会员国的普遍赞同,在全球具有无可比拟的合法性。尽管有这些有利条件,政策发起者仍难以在负担分摊的讨论等方面利用2030年议程促进经合组织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更大融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政策发起者还没有利用互惠互利理念和发展成果理念作为“吸力石”来将中国、其他南南合作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捐助国凝聚在一起。
全球发展的一大趋势是经合组织国家和中国基于身份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兴起,这阻碍了“吸力石”理念的融合。互惠互利、发展成果和2030年议程等有关加强多边合作的国际化理念正面临着总体不利的政策环境,并有可能在政治上遭遇强烈的反对。因此,政策发起者需要以政治上的明智方式,利用其政治权力和修辞技巧以弥合民粹主义与国际化多边主义理念之间的鸿沟。
*本章节英文版下载链接(点击阅读原文下载):
https://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978-3-030-57938-8_10
【CIDGA】新书系列四:协调争议,发展合作经验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
结论:利用发展合作经验,推动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关键信息和前进方向
(Conclusion: Leveraging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Experiences for the 2030 Agenda—Key Messages and the Way Forward)
本书最后一部分系统梳理了书中各章节的基本内容以及不同章节之间的关系,并提纲挈领地指出了本书的目标,即通过描绘发展合作行为体的演变过程、呈现日益复杂的多利益攸关方格局以及解释指导发展合作领域实践的规范和叙事,为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方法和借鉴。
全书主要有四点贡献:第一,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首要地位。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应积极采用新的发展合作模式,例如,具有分担、负担和共同承担风险特点的跨界协作等模式。
第二,本书从三方面对若干理论框架进行了讨论,包括援助的全球化和规范的传播、话语制度主义、协调、中等国家理论以及四C模型(合作、对抗、互补以及共同选择),以促进对框架进行更加合理的选择。
第三,本书各章节分析了在分裂、争议日益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大背景的条件下,通过国际发展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会面临的挑战。这些章节侧重讨论发展合作的不断变化和相互冲突的规范性观点、特定和重要的利益攸关方的作用、议程涉及的技术问题以及机构转变和新创建平台的需求和挑战。在此过程中,本手册还提到了《2063年议程》以及非洲希望实现的七大愿望,此内容在Sidiropoulos的章节得到强调,此外,Chan、Iacobuta、Haegele以及Weigel和Demissie还在章节中提到了《巴黎协定》。
第四,本书提到在有争论的全球治理成为普遍特征的情况下,超越争议来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几种方法、模式与案例,其中包括三方合作、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多中心治理等。
本手册旨在回答如何调和发展合作中的不同叙事和规范以实现2030年议程。我们提出了一个三步走的思路来思考这个指导性的问题:首先,我们更详细地概述在发展合作政策领域形成不同做法的叙述和规范。第二,我们探讨持续存在以及新出现的体制性争论场所。第三,我们还探讨国际治理结构如何更好地处理争论并加强协作。
本书各章通过描绘发展合作行为体不断演变和日益复杂的多利益攸关方格局,更深入地解释指导发展合作领域实践的各种规范和叙事。此外,这些章节还阐明了我们所说的“存在争议的合作的持续和新地点,特别是在设置叙事和规范、制度架构和国际治理结构等领域”。这些场所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在国际和多边组织内的谈判进程、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双边和多边合作,以及其他与发展合作有关的平台形式。作为有争议的合作全球格局的一个例子,Swiss在本书描述了援助的全球化在不同援助重点下的周期性动态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框架对这些不同的参与者和平台如何协调其对实现2030年议程做出的贡献提供了很少的指导。此外,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基础共识一直受到不断变化的政治动态如民族主义政策的兴起和全球集体行动意愿下降的背景,有几章探讨了如何进一步改善现有的全球治理结构,以应对争论和避免僵局;包括Chan、Iacobuta和Haegele、Mello e Souza、李小云和齐顾波、Engberg-Pedersen和Fejerskov、Kloke-Lesch以及Weigel和Demissie所撰写的章节。这些例子的两个关键类别是:行为者自愿为国际合作承担更大的责任,以及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下试行新的合作形式。
2030年议程所定义的可持续发展筹资是本卷所关注的一个关键问题。此问题在本手册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2030年议程及其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远比千年发展目标更宏伟。迄今为止,预期的融资机制还不能实现预期目标。很少有捐助国将国民总收入的0.7%用于资助官方发展援助,包括债务减免。虽然需要继续努力争取国民总收入的0.7%的承诺,但重要的是为及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调动大量资源。官方对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支持概念旨在对官方发展援助进行补充。各章节都承认新兴经济体在支持多边主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其中包括促进两个新的多边机构,即新开发银行(NDB)(俗称“金砖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Paulo、Seifert和Zaytsev的章节对此进行了详细讨论。
接下来,书中几章分析了发展合作行为体如何在不同区域推动2030议程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例如,Janus和Tang说明了中国在担任G20主席国期间如何推动2030议程并加强国家发展承诺。此外,本手册还有四个贯穿各章的贡献,代表了发展合作政策领域演变的关键发现:(1)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首要地位;(2)新的理论框架;(3)争议与合作;(4)超越竞争。
*本章节英文版下载链接(点击阅读原文下载):
https://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978-3-030-57938-8_33#Abs1